原创 久久无法释怀的少年时代(长篇散文)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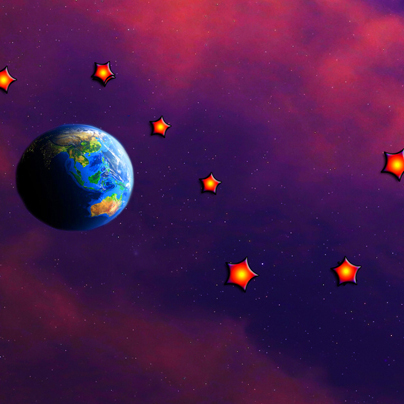
文丨曹旭
汉魏故都许昌有一条河,那是1800多年前曹操的运粮河。——题记

小院
满怀忐忑的孩子的夏夜,他的忐忑夏夜,没有星空,他躺在秫杆棚下面的凉席上,旁边是草屋檐下浅浅窄窄的水道。曾经的暴雨过后,那水的一部分滴入他们的伞上、碗盆和木床上,大部分顺着夯实的麦秆屋顶而下,在门前流淌,以水道为主流,未知流向何方。天晴之际,门前有棵瘦瘦高高的椿树,几乎高过草房,叶子也同样,在屋檐之上,之上是高高的蓝天,即使没有白云飘过,那上面是高高的蓝天。椿树之左,那个狭小的墙角,堆埋着一束青葱。
夏夜里的青葱,似乎依然闪亮着翠绿的色泽,新发的嫩芽,一根根的,在棚前一瞥,见它葱茏的一闪,惊喜的样子,安慰的样子,那种生长的力量,他总是观看宠物一样,每每在回来的时候,把它打量。而且,母亲最爱做的那一种面条,就是葱花儿面条。
先拔一棵青葱,剥去那一层带泥土的白皮,小心的掐掉根须,在房东人家的汲水台前洗净,切成细丁,放上盐巴,加上酱醋,倒花生米体积的豆油,有些姜更好,没有也无妨。如此腌上之后,煤火上的水已经烧开,先下面条,滚过两滚的瞬间,把葱儿料放入,起锅,乘碗,不怕热的一口一口的就食。那种清澈的香味,麦子的香味,葱花儿的香味,还有泥土的老本,掺杂着,柔和着,悠长悠长,一生一世。是啊,是葱花儿,原来的每每的一瞥和瞩目,是那破败墙角,瘦高椿树之下,有一小丛青青嫩嫩的的鲜花,在那里盛开,而且日渐清新,永远不败,在水中散发着香味,悠长悠长。
椿树之右,这小小的也称院子的椿树之左,还有一个奇怪的木桩,碗口大小,一尺多高,一半入土。那是他埋下的,他在那些杂志里面看到的一种硬功练习,据说是铁拐李传下的硬功,即用内脚踝长期击打树桩,日积月累,上身不动,下面暗出小腿,至敌方防不胜防,尤其矮小个子,下面攻击,天下无双。
如是,他找来那根木桩,埋在院子里,屋檐之下,从轻轻的五十腿,左右两脚,到有些疼痛的五十下,再到一百,复则二百,早晚两次,天天不断,无论雨雾,计为三年时期,即可神功在身。那神,在椿树之上,远远的看着这个少年,在小院里,一脚一脚的把迷梦击打,一声一声的夯实着沉睡的灵魂。
只是常常,那木桩被踢歪下去,成七十度角,向一尺外的破墙倾斜,他要耐心的把它扶正,用那根木棒,夯实木桩的土基,之后再把它踢歪下去,再重新复原,如此反复反复。就是他的院子,两平米天光,两平米地域,却是一条通往天庭的迢迢征途,一丛生机盎然的翠绿鲜花,一桩坚实艰苦的壮丽梦想,在那些忐忑的夏夜。

马步
一周之后,光明剧院的那个早晨考试过去了一周,传来一个惊喜,刘老师,那个高大威武的教练,传话让他明天早晨到光明剧院跟他学拳。原来,刘老师出差一周,已有空闲,便通知这个喜讯,他被刘老师收为学徒。
武术的手,是一棵树木上无法表述的枝杈,其掌其拳,仿佛在杂乱的形式间鲜明着直径与弧线,在那个绿叶开始浓稠的初秋,武中的掌,砍向颈部的动脉,一霎之间,阻断头脑与心脏的血管,那人像妖一般顿时昏厥;武中的拳,四指向掌心回拢,拇指叠压而上,拳面直线出击,是腥腥的鼻血,弧线太阳穴位巨大撞击之后,依然是无地无天昏天黑地的昏厥。
当然,这一切的技巧,还在于基本的土壤,在于整个身体的展开与拉伸,在于筋骨的基础夯实与强筋,腿之筋如何以伸展而遒劲?则压腿,一腿支撑身体,一腿从体侧放置在冰糕房,后来是在子弟学校的窗台上,勾起脚尖,一臂上举,一掌立于胸前以虔诚的摸样,两腿伸直,腰部挺立,指示身体向冰糕房和子弟学校的窗台振压,振压幅度逐渐加大,从夏末到初秋,从旭日到圆月,在自己的身体内如此艰辛而幸福的长征。
腰也是不可少的,并步站立,两手十指交叉,直臂上举,手心向上,向蓝天的方向,之后上体前俯,挺胸塌腰,两手向大地的接触;那少年的双手,经过腿腰的万重阻碍,一振振,一点点向大地接触,触摸大地的温度。寂寞了,把两手松开,用双手滕饶双腿,抱紧双腿,像紧紧的抱住一根梁柱,抱紧自己的命运,尽量使自己的脸庞,向柱石贴近,那些正在成长的柱石。
肩功是两脚开立,他与胖红扶着对方的双肩,先是抬头挺胸,然后塌腰相振,向下向有些眩晕的大地与两个少年心灵的广阔空域振压。他个子矮小,在有些高的胖红的双肩沉着,他几次失手,一次碰上对方的头,一次双手那么似乎是缓慢的落在汗水滴满的土地。胖红,他,还有另两个少年,一同被刘老师收为学徒。
比较韧性,不仅在腿肩,还有的是那种马步站桩。两腿迈开,与肩同宽,在晚夏的早晨,初秋的傍晚,双手握拳,置于腰间,屈膝下蹲,若骑马状,并不在草原,而是河南许昌的运粮河畔,河西之畔的碾上村落。做骑马状,在那里踏实的奔波,原地不动的奔波,虽不腚下有高香袅袅,头顶无碗水莹莹,但他们四人一排蹲好,刘老师在周围散步,或者走将过来,在谁的腿弯处踢上一脚,而他背对少年们的时候,被踢的人会站起来,那酸胀的双腿趁机喘息,老师回头的瞬间,那双腿已经马步,屏住了呼吸。
远处的朝阳,已经越过了子弟学校的灰瓦灰墙,那排教室的房脊,高大的杨树,俯视着几个蹲桩马步的少年,路过的几个少妇,不时把他们指指点点。他要坚持,他个子虽小,却要战胜所有的师兄,且要战胜的是自己,自己营养不良的身体,赢弱的身体,汗泪不辨,屹然不动,仿佛傲气,他站在地上。复站云端,他看到草屋,看到不远处的棚房,他和母亲的新的棚房。他站在地上,立于云端,终于他倒了下去。
刘老师对他的母亲说,营养不良,晕过去了,这孩子太拼命,买点儿鸡蛋吧,补补身体。不知道母亲是否应允,只知道当时的马步,马步对面那棵高大的杨树,一振一振的哈腰点头,像腰肩的功,那些碧绿树叶的枝头。

棚屋
马步桩站晕过去的时候,是在子弟学校家属院内,她和母亲已经搬往子弟学校及家属院一体的一橡胶厂家属院。母亲那是决绝的,在一个放学的傍晚,在地窝一样的草房内,母亲拉他过来,两人并肩坐在床头,母亲流泪说,房东的男主人下午过来了,说要是不嫌弃,请母亲去他的北屋。他已经十三岁了,他知道什么意思,他猛然而起,从木门后面抄起那根木棒,拼将出去,母亲拦腰抱住她,母亲只是说自己的屈辱,他只要儿子一个依靠,只有儿子眼前这个亲人,她无言以对那周遭冷酷庸俗的世界,但,她不让年少的儿子拼命,她决绝要离开这间草屋。
他无从泄愤,听从母亲,只是在一个不知什么季节的夜晚,他从碾后的街,向草屋的院落里,一连扔进三块砖头,那毕身的力量,把砖头扔向那家房东的院落,如同他曾经把石头射向,那父亲所谓那有了的女人的窗户玻璃,那个女人在父母离异之前,已经和父亲来往,那个可恶的可杀的,那也算个人么?
母亲决定搬迁,是在学校背后,在家属院北墙盖一所简易房子,简易棚子。那个年代,她申请不到家属院的楼房,三栋楼,一新两旧,三层四层,六十户左右,她申请不到一间,那就仿照别家,在校园北面四楼后的北墙上,盖上简房一间,可以驻足落户。

依北墙而下,垒上二四的墙,一砖竖一砖横加上灰泥的二十四公分的墙,加上三根檩条,交叉十几根纤细的椽子,上铺一层高粱秫杆,一卷油毡从墙头滚展而下,然后五竖行红砖压伏,尚有南东两面小窗,地铺红砖,那是他自己夯实地面,一块儿一块儿铺就的红砖。得,九平米的棚房房子可以搬住。当然,垒墙建房的是表哥他们,窗户及檩条椽子也是娘家帮助,红砖应该是自己购置,他记得,母亲从姨家借来了二百块钱。如此,一个新家有了,属于自己的家。
一张木床在墙西,搬来一张课桌在南窗下,没有花,但春节的时候,买来一张画,十二金钗图的画,红楼里的那些画;窗有翠帘,青竹图案的布帘,东窗有方桌。母子二人用剩余的红砖和油毡,依东门顺墙势而上,塔起一个两平米的棚子,可以放煤,可以置台,可做厨房,厨房灶屋,还听到一侧幼小的梧桐上,麻雀在上面跳跃着鸣叫。
喜悦之余,冷秋的寒中,风雨骤至,幸好他在不远,而且一家邻人已经过来帮忙。那狂风已经掀开半个屋顶,裸漏屋的消瘦肋骨,黑褐色的肋骨,见那内里的床铺,那口黑红色的木箱,那方黑红色的矮小木桌。
走上去,在邻居大叔的帮助下,他攀上北墙,走上去,把油毡一手一手的铺原,沿着单薄的泥土垒成的二十四公分的砖墙,在凛凛寒风却已稀微的雨中,把折叠的房顶一尺尺的展平,再接过邻家好人及母亲递上的砖头,一寸寸的压平,仿佛看到母亲在厨房,那两平米的灶火上烙馍的身影。
他呢,在学校的水房寄住,那棵高大的杨树下学校的水房,五平米多些的水房,是学校打铃人的办公室,晚上可以在那里寄住,深夜他可以杨树桩练腿功。傍晚他和师兄弟在学生说散去的教室门门前踢腿,最矮小的他,排头领着师兄弟转圈踢腿,在水房的西面空地上马步站桩,直到把自己站晕过去,地上没有泪水。
母亲站在楼北的地方喊:“回来吧,吃饭了!”寒风从北中国的辽阔地域,横黄河而来,嗖嗖落入运粮河畔,还有运粮河畔的棚屋人家。

面粉
春节是要包饺子的,他的商品粮关系,是在上初中不久,经过父亲的努力,从乡下办到城市。还记得父亲在农村那座瓦屋里趾高气扬的从东屋扬帘而出:“来,来,来,看看这是什么?”父亲拿出的是他母子三人的粮本,已经离开农村可在许昌城市内购粮的那种证件。父亲从东屋趾高气扬的扬帘而出。那是那个父亲吗?
离异之后的母亲要养活他,并不费多大周折,法院判决综合考虑,手足弟弟跟随父亲,他跟母亲,判决还是在那间草屋内,母亲半躺在床上,在幽暗的光阴中,母亲好像半躺在床上,对他郑重其事的说:“我要告他私藏军火弹药,预谋叛国!你看咋样?”非问之问,非答之答,你能如何?他当然顺从母亲的心意。当然最终的结局是,什么叛国弹药私藏,每月父亲只是应付工资中的十元钱作为抚养费,其它皆是闲扯。
每月的十元钱,他第一次在五一路水泥厂办公区的会计处领取。从五一路水泥厂的大门进去,在漫漫灰尘中,找到会计室,坐在长凳上,等候领取抚养金。虽然只有那么的一次,父亲像去年暑假给他费用,威逼他离开书摊生意一样,他自领取了第一次费用之后,父亲传话他直接到父亲手中领钱。他拿到十元钱之后,在水泥厂大门口的北面,那运粮河的岸边,五百米之外的岸边,大口的喘气,在那一桩桩法式梧桐的一侧,在那缓缓之流向南方的运粮河水一侧,大口的喘气。
面粉的价格没有追究,十元钱应该有相当的粮食,不是第一次的十元钱,只记得在五一路粮店,从文化路迁移到五一路粮食户口五一路店,称粮食的是一个青年人,如若后来可以想相约饮酒,或者邂逅对杯,该是怎样的奇迹,是无处不在的痕迹?那青年也许看错,甚至故意,不知道什么关系,他要买的面粉是十斤,那青年却称上四十斤的面粉,他的手里是一银亮的铲子,在雪白的粉堆上,一铲一铲的给不同的人家,那严肃着应该是俊朗的脸庞,不知为何,却给他四十斤的面粉。

买十斤却又多出三十斤的邂逅,他有些紧张,却忍着不能多言。他提起那些超重的面粉,是春季将要到来的那种喜悦。他掂起似乎四十斤的果实,那些白白的面粉,那些运粮河畔碾压过的,运往黄河之北颍水之南的面粉,在后车的座上,在那辆残破的自行车上,惊讶而兴奋的逃离,赶快离开粮店背后的面粉厂,刚刚回家,几乎已经忘记那是临近的春节,整个冬天没有飘雪。
母亲只是问,怎么这么多?他应该没有和母亲说什么。几天之后,那除夕的街头,已经来往的没有人迹的街头,天上飘下雪来,预备饺子和年夜的小城人家,在热气腾腾的厨房忙碌。母亲贴上春联与门神,在那棚房棚屋,他知道饺子盘肉太少,他说要出去一趟。除夕降临的五一路中段,飘雪纷纷而下,少无人痕,水泥厂之北面,运粮河之西的五一路口,五一路中段,竟还有两人,支撑着木架,悬挂着卖肉,仿佛专迎着雪花飘飞中来临的人家。五花肉,肥肥的,一个少年,用囊中剩余的所有钱,让那些生意也是自家买卖人的兄弟随意切割。应该是那样的,雪花飘落在买卖人兄弟的发上肩头,飘落在他手捧年货的脚步上。白面及饺子,腾腾的热气,在棚屋的小桌上,那伴嫁母亲的小小方桌上,冉冉升起。

煤球
乱搭棚屋就要改造了,无处安生的母子两人,有人出主意,不是不分你们房子吗,厂里副厂长调往市内任职,现房空着,你们把房撬开只管搬进去,你孤儿寡母,谁有如何?母亲按照善意,领着儿子硬搬进去。两间的房屋,进门即是厨房,母子一人一间,有些奢侈。当然,不久之后,一橡胶厂有关部门,左右无法再来为难已经无助的孤儿寡母,勉强着,也是由着心中的善良,分给了新楼上的一个小套,三十多平米的房屋。他在厨房改成的书屋内,将要阅读大学的课程。
寄居在棚屋与两楼两居室的岁月,最难忘的是拉煤了。严冬到来,母亲借来木架子车,他一个人,越过温暖的运粮河水,向东直行,在铁路线的南侧,在解放路东面,整个土地都是黑色的,煤屑从京广线的铁道上乘车而下,制成蜂窝煤,又被搬来搬去的途中,洒了数年累月,整个地面是黑色的。那个严冬,他一个人拉着架子车,不是走铁路的南侧、水泥厂北墙的路线,不是两千年前碾上粮食运行的路线,而是走铁路以北,越过运粮河水,经解放路向南过铁路线,向东一侧,到达那全市唯一的蜂窝煤厂。
那个严冬,买好的煤块儿,师傅点过数目,他五个一摞四个一摞地搬到一棵落叶的梧桐树下。冰冷坚硬的煤块儿,仿佛有着一颗不会燃烧的心。他只能拉动一半的煤块儿,到家之后,仍是一摞一摞的搬到棚屋里面,跪放在母亲的床下;一趟一趟码好摆齐,然后匆忙转头,重渡河水,走进煤场。

那条河流没有结冰,他好像认真的打量一样,那曾经滑入温暖河水的堤岸,那暖暖的流水,似乎有微渺的热气向上蒸腾,如幻微烟,渺渺的热量,温暖的缓缓而不绝的向南流淌。往往在夏季的一场暴雨过后,有一种大人口言“翻坑”的现象,大概是河水缺失氧气的缘故,会有千百的鱼冒将出来,原先他们都隐没在深渊河底,暴雨过后,千百一掌两掌长的鱼儿,几乎一下子浮于河面,引来不知平日里匿于何处的渔夫,搬来一种一丈平米的网,四角兜着,一个竹竿撑起,放置河水之中,不时拉起,网中便有跳跃翻腾的鲫鱼鲤鱼,一桶又一通的收获,也有传统的那种撒网,甩撒而去,一网拉起,也会有多条的鱼儿,在地上网内,含蓄在水草之间,喘息着翻跳。而此冬天的一瞥,运粮河水,无波无澜,如梦如幻如烟,向南涌流缓缓。
剩下的一半煤块儿,整齐的放置在树下,那梧桐的枝头树丫,只剩几片枯萎的残叶,在寒冷的气息里,不时痉挛着摇晃一下,虽早已死亡,却不坠下,一只不知何处飞来的麻雀,坐落在一根树杈之上,又突兀的飞走,干瘦的树枝,在它赤裸的足下,与其飞离之间,不为人知的优雅颤动,终于有一只如手指紧缩成虚团的桐叶,在那枝头摇摇晃晃的飘下,萎靡不振的落在那一堆摆放整齐的煤块儿上。在没有太阳光辉的天下,煤块儿却不时闪耀着微小的银光,是煤屑中特有的那种亮光,而更多是冷气中降下的寒霜,一抹一抹的银亮,
第二车的煤块儿拉回,他已经满头大汗,脱下的棉袄搭在车帮,只剩母亲剩下的那件红蓝相间的纤维薄毛衣,依然蒸腾着微微的热气。母亲也许在上课吧,给他的学生补课?只有他自己,一个人拉着半车的煤块儿,低头躬身来去。幸好后来有胖红看到,从远处跑来帮助,否则不知要有多长的喘息。
周日的寒冬,煤块儿在炉火中渐渐燃烧,红焰复辉煌的燃烧。春天,正从远处姗姗而来,一场大雪将在深夜,静静的把中原大地轻柔而严实的覆盖;春节,将如一轮旭日,从东方盈盈艳艳,喷薄而出,平凡的世界,竟如此晶莹而鲜艳,妩媚而壮丽。

结义
跑步是基本的训练,他定下目标,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,即使是大雪大雨的早晨,他依然坚持跑步,一日练一日功,一日不练十日空。元旦节的早晨是雨,冷冷的雨晨,他穿雨衣,那种军人的雨衣,胖红送给的雨衣,着雨衣从碾上后街出发,一路向东,在黑暗里,向也许不久便会雨过天晴的东方迅跑,穿过五一路,逾越运粮河,到解放路,新兴路,文峰路,延安路,回归到碾上后街之西。那次近三十里的跨越,到终点他几乎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,意图和意识之间已经错位,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,在冷冷的雨中。春节的大年初一,他依然是没有停下自己的锻炼,不是抹去发梢上的霜白,仿佛看到晶莹的微微燃烧的雪花,从不知何处的天野,永不休止的飘舞。

春天来了,运粮河畔有迎春的花,黄艳艳的冉冉开放,胖红在四层新楼的后面,母亲原来棚屋的西面,已经吊起了沙袋,木屑与沙子相搀,年少的拳击不久,血从小指到无名指间逐渐渗出,再到无名指与中指之间,如月季的鲜花一样灿烂。他们无比欣慰,自豪着自己的意志和磨坚。他的脚功也没有中断,水房前的那棵巨大的杨树,是真正的树桩,而且刘老师教会了靶掌,一左一右,双掌向白杨,如脚功的轮回,一次左右一百,如晨步相续,直到可以右掌推击灰色的墙垛,可以推下墙砖的一角。那时的八卦掌太极桩,已经从他的脚下缓慢升起,在掌中款款柔转。胖红不知从何处打来碗口大的六根木桩,栽在新楼之后,在其上行走八卦,在梅花上徐徐的旋转,那梅花之桩。

春天来了,运粮河畔的光辉洒在他们逃学的堤岸,正在萌动的青草,还隐蔽在往岁野性的枯黄草丛之间,他们两个还有另外的伙伴,在灿烂的阳光下,那个辉煌的下午,第二节课就是放学了,在河堤岸上,点上三根枯藤的枝为香:“生不同年同月生,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那些可怜可爱可惜可敬的少年。他们三个结拜结义。其身之侧,运粮河水,潺潺的涌流,千年以来,源源不断。水泥厂的那些梧桐,那里落满了厚厚的灰尘,河水之上的铁桥铁线,那里散落的足迹,河畔之西橡胶厂子弟学校的那颗高扬,那些寒星和春夜里的身影,千年以来,仿佛不断,如流水流音,脉脉无声,绵绵不绝。

(完)
☆ 作者简介:曹旭,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,笔名陈草旭变,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、小说见散文在线、红袖添香、古榕树下、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,合著有人物传记《那年的烛光》。
原创文章,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
编辑:易书生